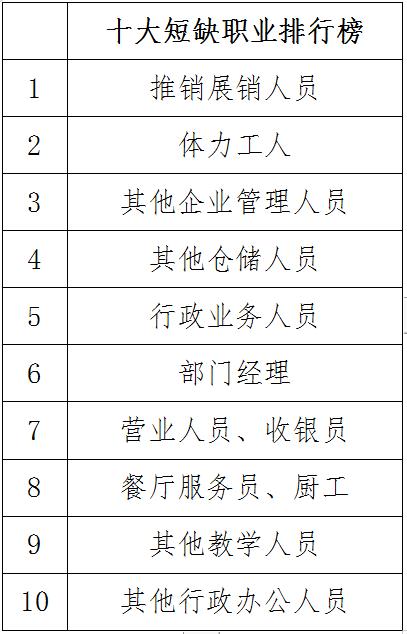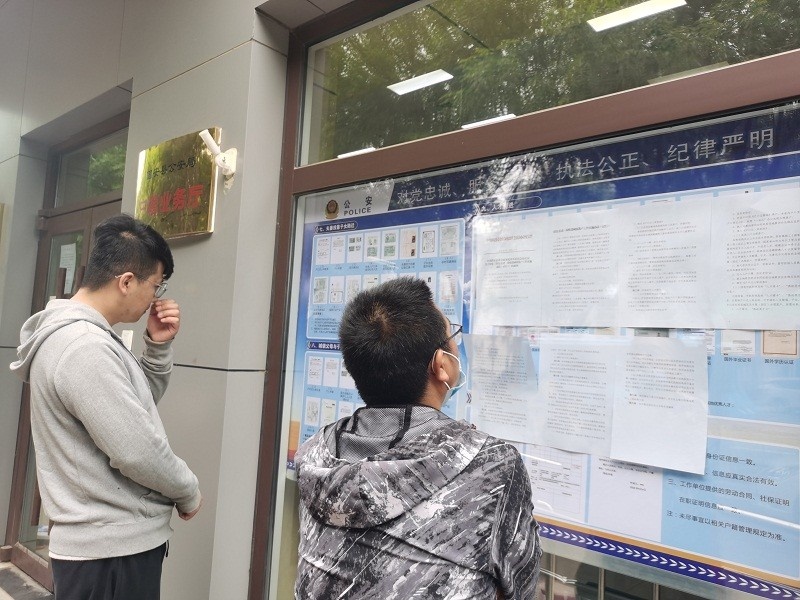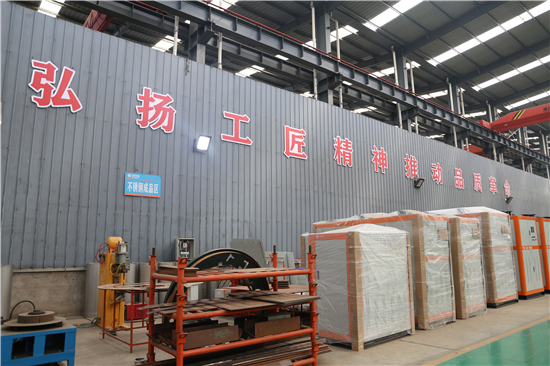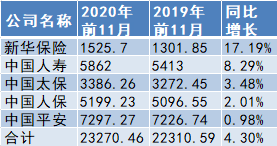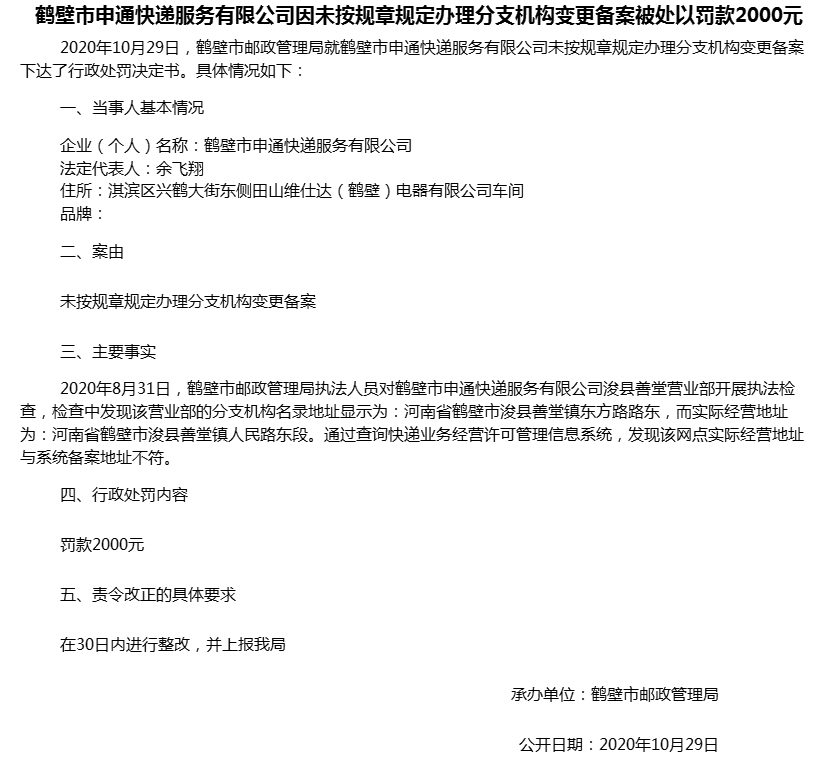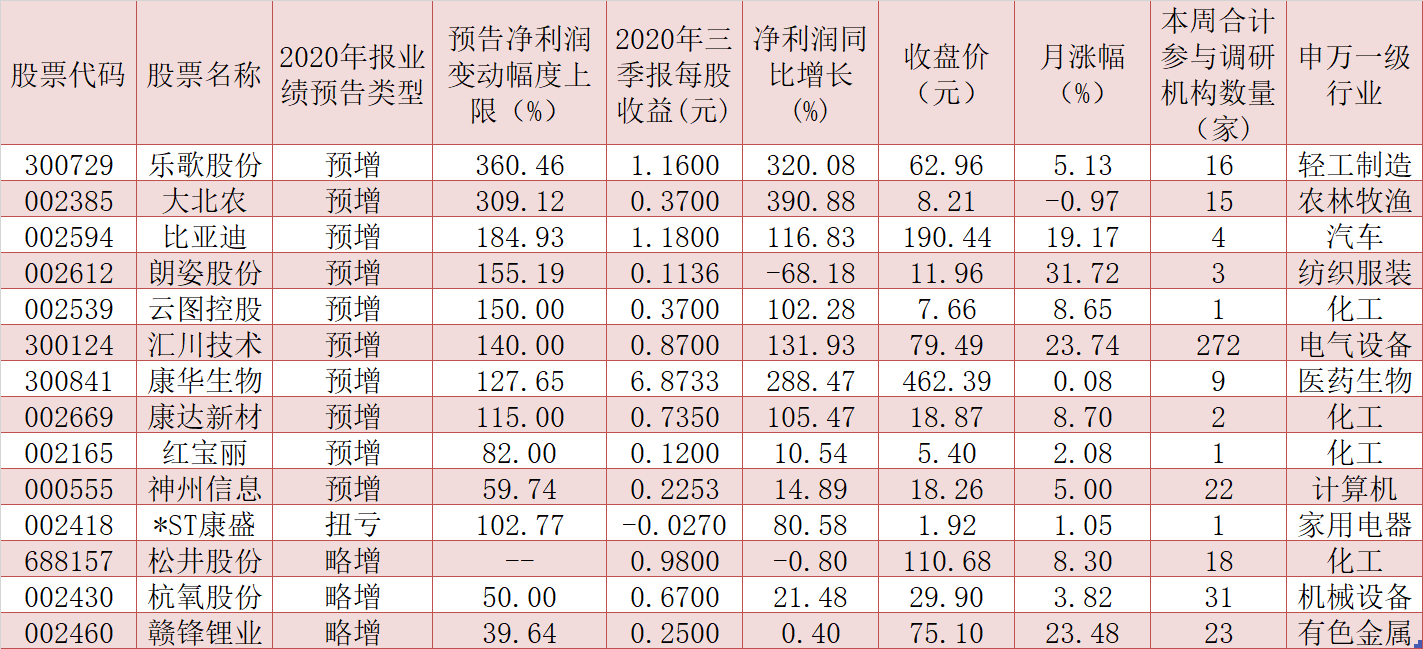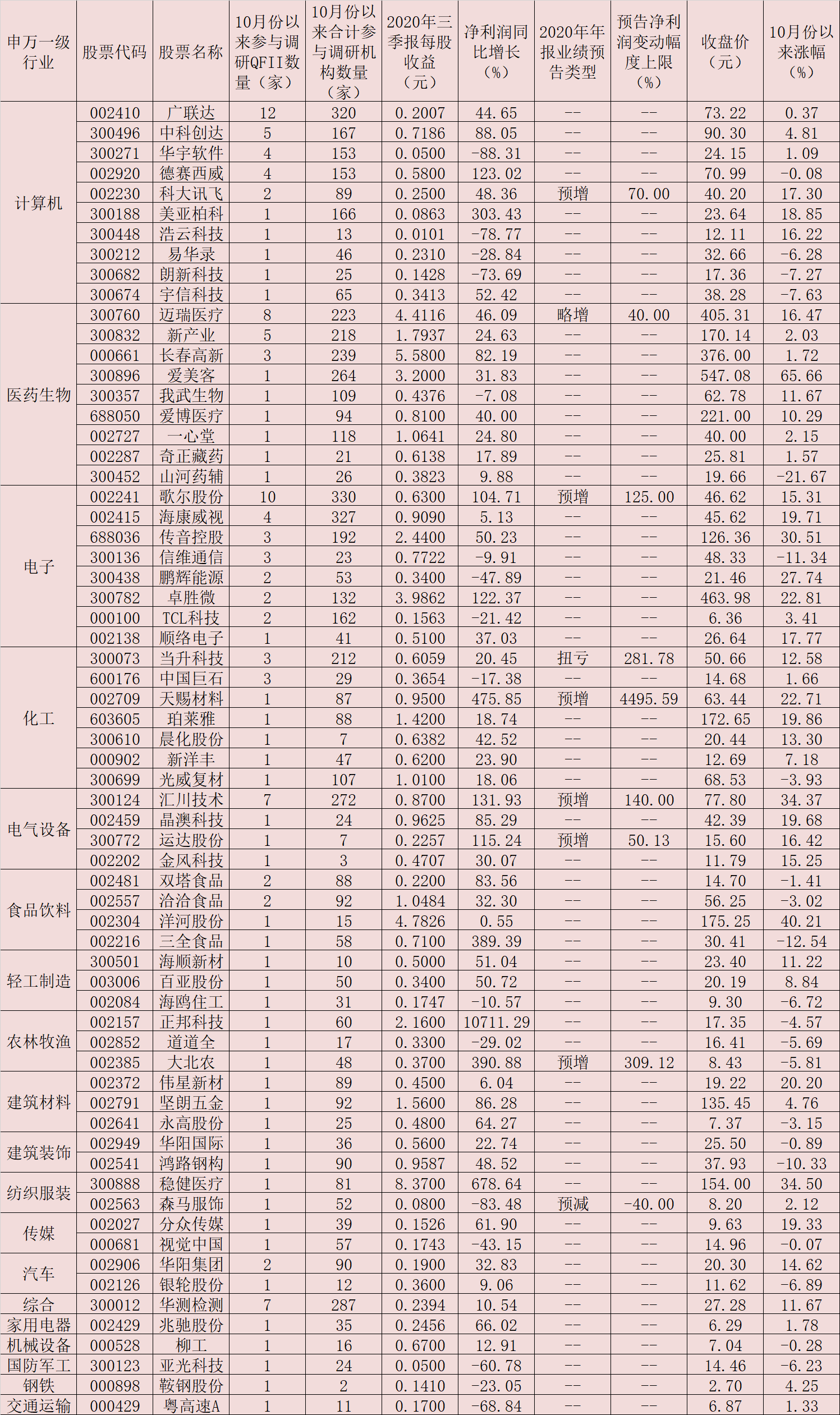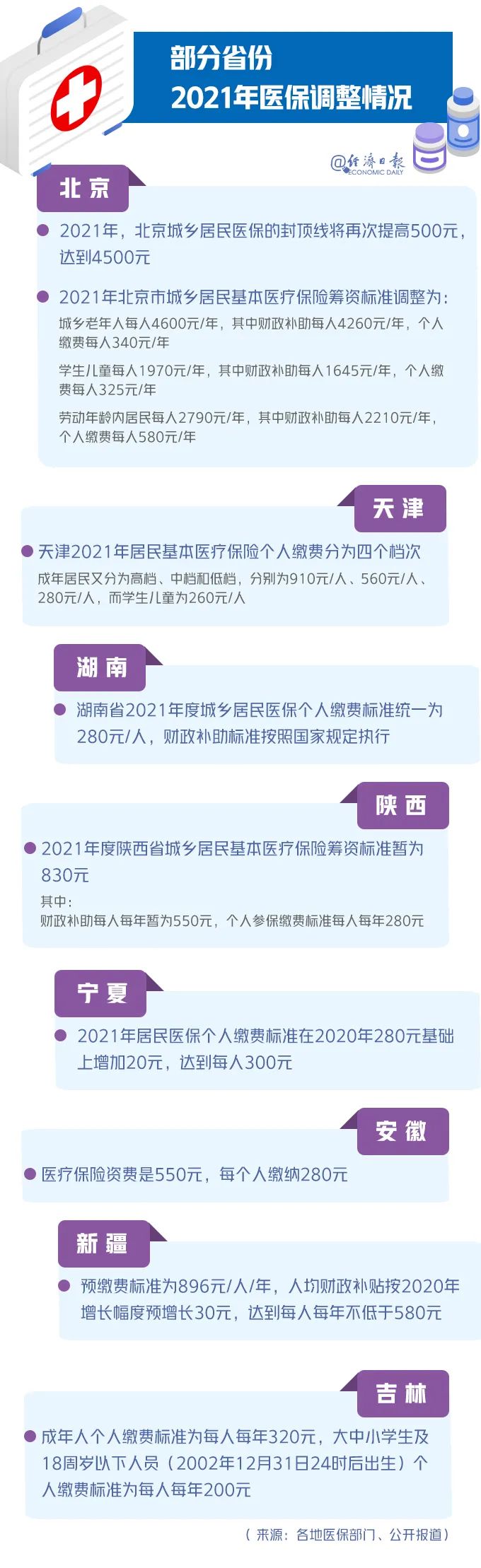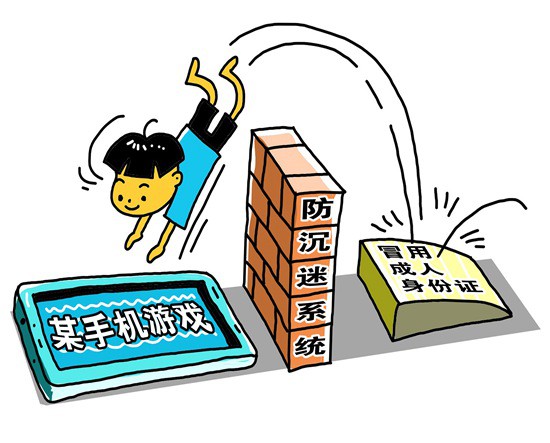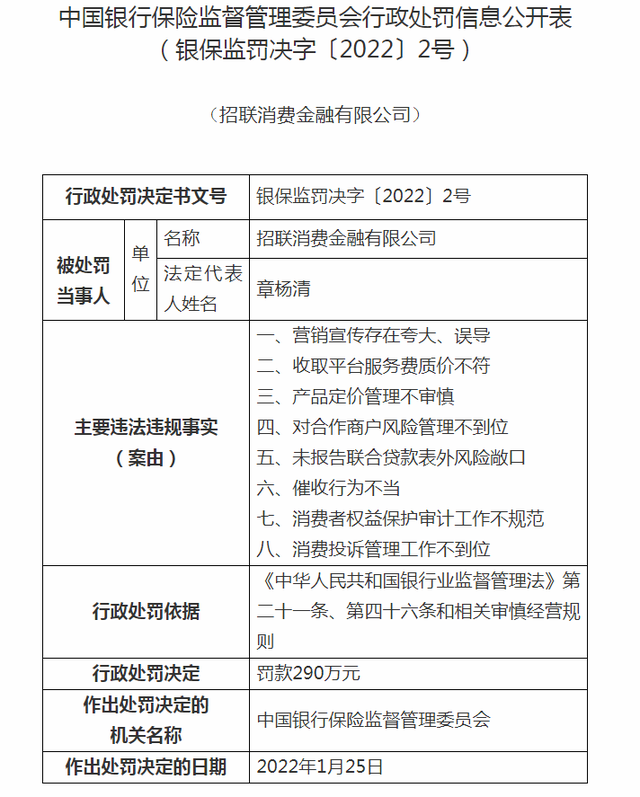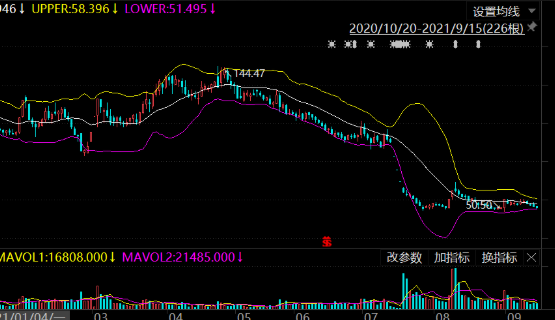原标题:张艺谋:大隐于技艺的手艺人
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得到一面倒的好评,但这没有逆转张艺谋和女儿张末联合导演的《狙击手》在电影市场的境遇。《狙击手》的排片仍然有限,票房数字缓慢小幅地爬升。在这个春节档的非动画类电影里,它的口碑最好,社交网络得分最高,截至目前的票房却最低。
电影市场的现实,远比张艺谋长久以来的创作态度更强硬。72岁的老导演可以在体育场的大型演出里点燃全民的热情,但他的大银幕作品更多是圈层窄小、且年岁渐长的观众走进影院,被他执着的手艺人的态度所触动。
整个电影行业面临创作者和表达方式迭代,张艺谋反其道行之地放下他的风格标签,在一部紧接一部的类型片创作中,专注于锤炼老派电影匠人的技艺。《长城》之后,不断有外界的评论认为张艺谋放弃了“作者性”并逐渐丧失在顶尖影展中的对话和交流能力,《影》《一秒钟》《悬崖之上》和《狙击手》这些电影,的确佐证他从外部视角下的“作者导演”调转方向成为极度本土化的类型片导演。不久前,他接过职业生涯中第十座金鸡奖奖杯时,说道:“导演是手艺人,要恪守工匠精神。”这可以理解为一个老年创作者谦逊的自白,他坚持且实践着的这份“技艺之道”,在中国电影工业的大环境里,是否就像这届冬奥会的主火炬,是一簇冰雪里的微火?
把“个人风格”让渡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类型化叙事
如果因为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而走进《狙击手》的放映厅,会发现这是气质截然不同的两个作品。执导冬奥会开幕式的张艺谋仍是明确的意象制造者,直观的层面,追求技术和普通人的共同在场,形而上的层面,意图用发达的技术美学方案输出古老东方的价值观。事实上,这套创作思路在2017年的观念舞台演出《对话·寓言2047》里预演过一次,当时张艺谋制造了总共七组关于对话和寓言的视觉意象,并置古琴和激光、京剧和i Pad、碗碗腔和全息投影……舞台上的顶尖科技美学直接混搭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在某种程度上,这套美学趣味和张艺谋的武侠大片——从《英雄》到《长城》——同根同源,表达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视听想象。在视觉美学非常突出的架空历史题材的《影》里,张艺谋仍然用这套视觉趣味冲击着观众。但在那之后,从2018年至今的几部电影里,包括《一秒钟》《悬崖之上》和《狙击手》,张艺谋克制了自己的视觉话语能力,或者说,他把“个人风格”让渡给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类型化叙事。
《悬崖之上》可说是一部老套的谍战剧,英雄、圣徒和恶棍是典型人物,“螳螂捕蝉,黄雀在后”是典型谍战戏剧框架,即便如此,在一个很难劈出新的视角和破题思路的套路里,导演创造了一种扣人心弦的节奏,通过极简的叙事和黑白分明的伦理观念,完成一则“致敬隐蔽战线”的信仰童话。一旦进入“敌我斗争”的框架,正邪对立的人物关系里,敌人承包人之恶,张艺谋过往电影里反复表达的对人性的不信任、对救赎的怀疑,就拥有了合理性和正义性,而不再是可能冒犯到观众的。
《狙击手》重塑了青春片这种类型
《悬崖之上》是在既定类型内部的创作,相比之下,《狙击手》尝试了几个类型的混搭,打散并调度了历史剧、传记片和悬疑剧的部分元素,最终重塑了青春片这种类型。但《狙击手》带来的最大冲击力并不在于类型融合的大胆灵活,反而是影片内在的工整,它的严密控制的剧作和严谨执行的拍摄完成度,让许多专业的创作者心动。某种程度上,《狙击手》让人们看到张艺谋以老练的过来人的身份,既是师傅又是搭档,带着女儿完成一次剧情片的标准化操作。
其实,《狙击手》是在抗美援朝相持阶段这个特殊背景下,展开“成长”主题的青春片,创作者把老生常谈的命题搁置在非常语境里,实现一种陌生化。这“青春”的确很难让年轻观众共情了,就像片子里的旁白,这是“一切都过去了”的回望,是对血色青春的凭吊。12年前的《山楂树之恋》里,张艺谋借“少年纯爱”的名义,暗度陈仓他对历史的态度,为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史留下一抹宛如山楂花的传说。《狙击手》也是青春和历史之间血泪交融的复调,在战斗英雄传奇和战争历史的事实缝隙间,成长的集结号嘹亮又让人心碎。
围绕着张艺谋的不是杰作傍身的光环,他的最显著特征是手艺人的坚韧
这是一部从“小”处着手的电影。整个剧作框架的体量是小的,仅仅围绕一场阵地战。人物关系网络是小的,最初是一个班的战士,后来是两个人的对峙,最后只有一个人血战到底。戏剧场景是小的,一个阵地,两条战壕,单一场景到底。戏剧事件和悬念也是小的,一个美国狙击手以志愿军伤兵为诱饵,要活捉中国神枪手;志愿军明知遭遇战是陷阱,但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回那个身份尚未暴露的侦察兵伙伴。编剧和导演在看似迷你的格局里,展开了围绕着青春、战争和历史的多层叙事。在一场无名的战役里,血腥的杀戮摧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同伴们,然后夺去他视为精神支柱的前辈,孤身幸存的他必须背负所有人的意志,战斗到底。这个年轻人最初是救同伴,然后是救情报,最后,微渺的他成为推动历史力量的一部分。
《狙击手》的剧作结构和节奏里渗透了一种模板式的标准精确,具体到每个情境、每场戏像齿轮般卡得一丝不苟,可以认为这样的电影里缺少从容的发挥,也可以说,它是有些匠气的。但《狙击手》让人伤感的并不是它的雕琢感,正相反,这部片长仅95分钟的电影提醒人们,能控制在100分钟以内三幕结构剧情片,如今竟是稀缺产品了。当代商业电影的主流选择用松散的叙事铺陈无节制的视听奇观、电影片长动辄失控到150分钟甚至更长,《狙击手》这样的电影是调转船头逆流而行,老派手艺人不惮于“匠气”的嫌疑来证明电影古典主义的三幕叙事仍是可行的,100分钟足够展开浩浩汤汤的历史图卷,以及消隐于其中的青春碎片。
自2016年《长城》的惨痛失败之后,到去年底以《悬崖之上》再获金鸡奖,再到这部《狙击手》,围绕着张艺谋的已不是杰作傍身的光环。他的最显著特征是手艺人的坚韧,一部接着一部地拍片——《一秒钟》《悬崖之上》《狙击手》,在这些表达空间有限的电影里,或不断尝试类型的拓宽,或追求精益求精的剧作技巧和拍摄技艺,或对白纸一张的演员作出点石成金的指导,再多的失败和失意都不会影响他开始“下一部”。这些电影淡化了艺术电影的个性,也见不到文人电影的抒情和知识分子的三省吾身,但创作者还是有表达的,哪怕这些表达看起来过于直白而输了余味:比如《一秒钟》里听着“风烟滚滚唱英雄”潸然泪下的年轻人,电影散场后却难免一场群殴;比如《悬崖之上》里无休无止的落雪,风雪如晦黯家园;比如《狙击手》里,幽灵般奔跑在中美阵地之间的朝鲜孩子。
也许,可以把《狙击手》里的血战到底的大永看作张艺谋的自况:挺住就是一切。他两个多月前的那段金鸡奖获奖感言,老骥昂扬的斗志中多少掺了些感伤——这样的电影匠人越来越少了,并且正在势不可挡地老去。(柳青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