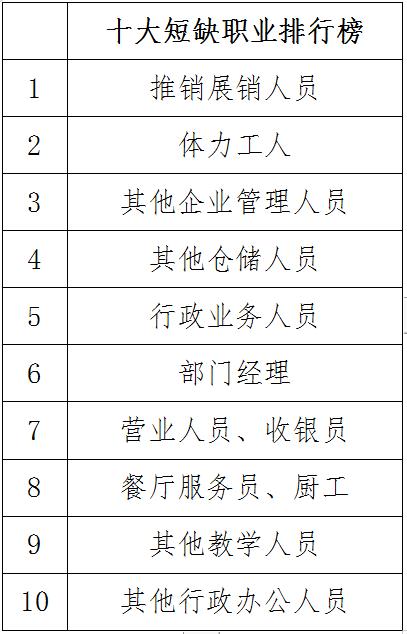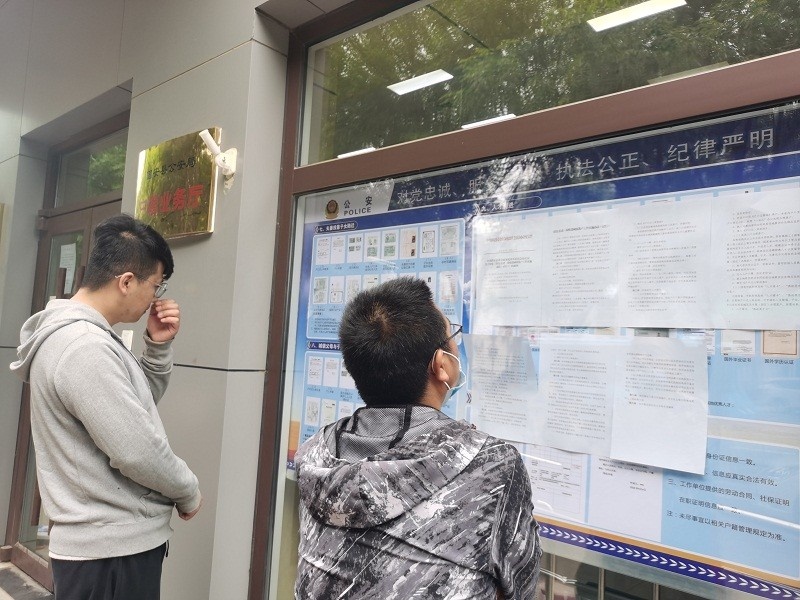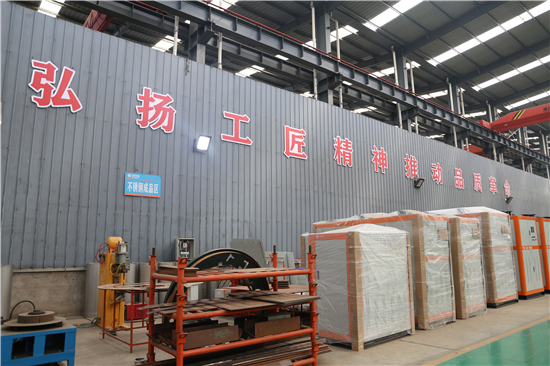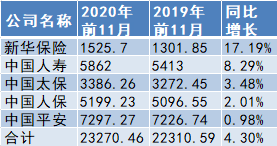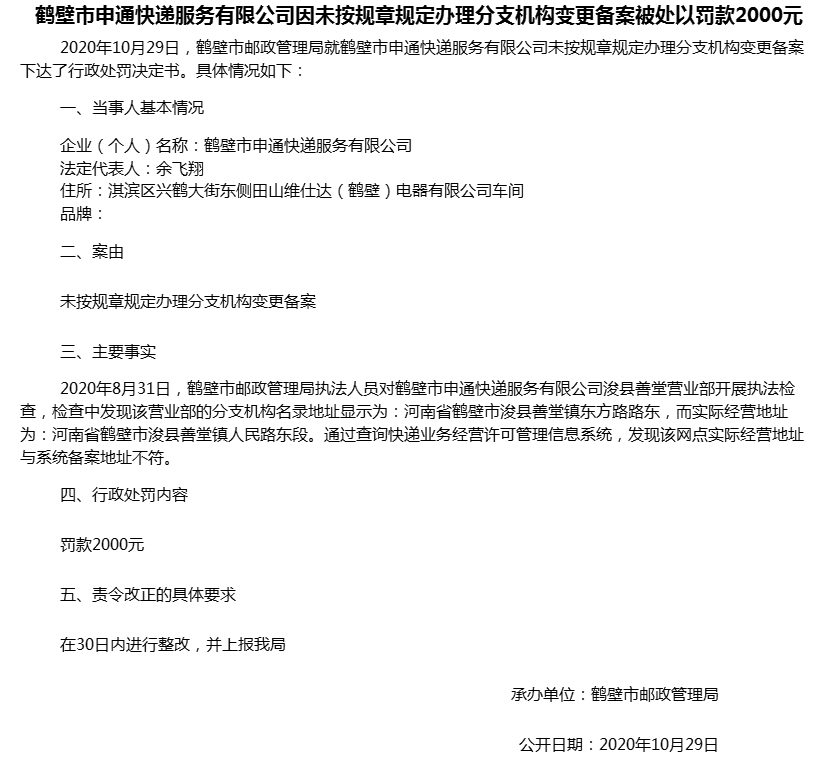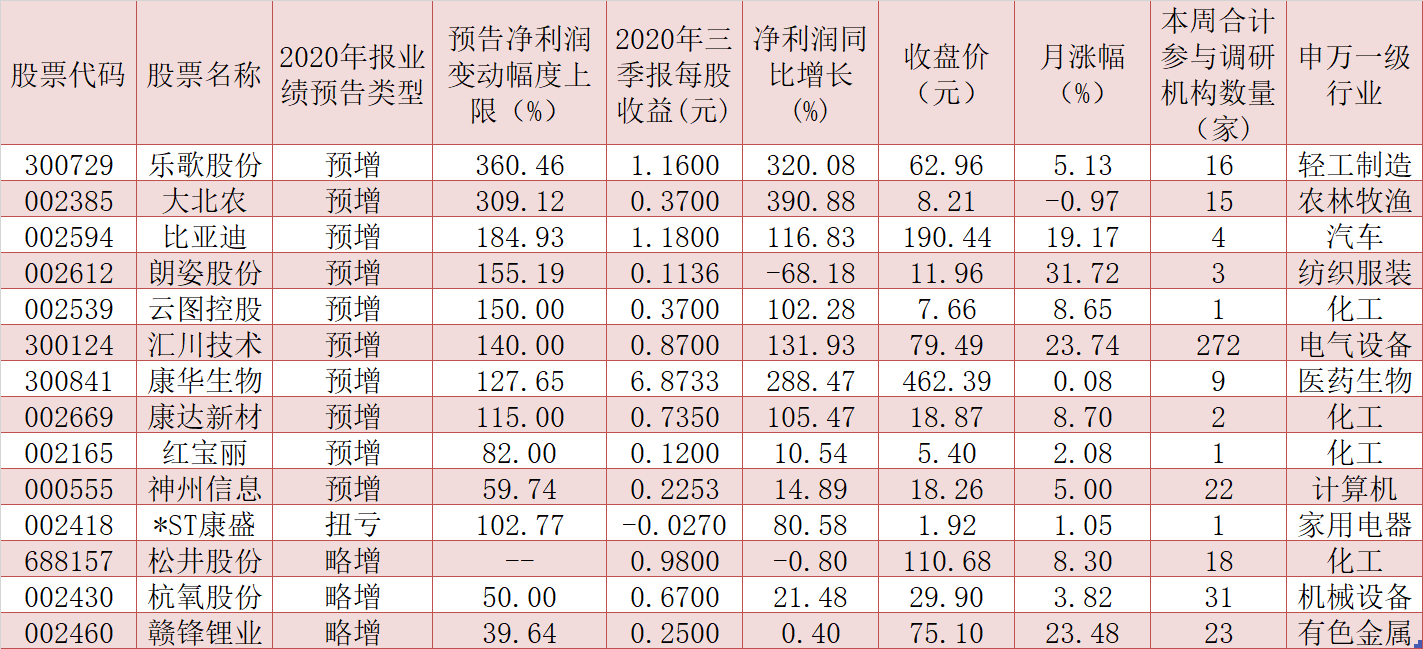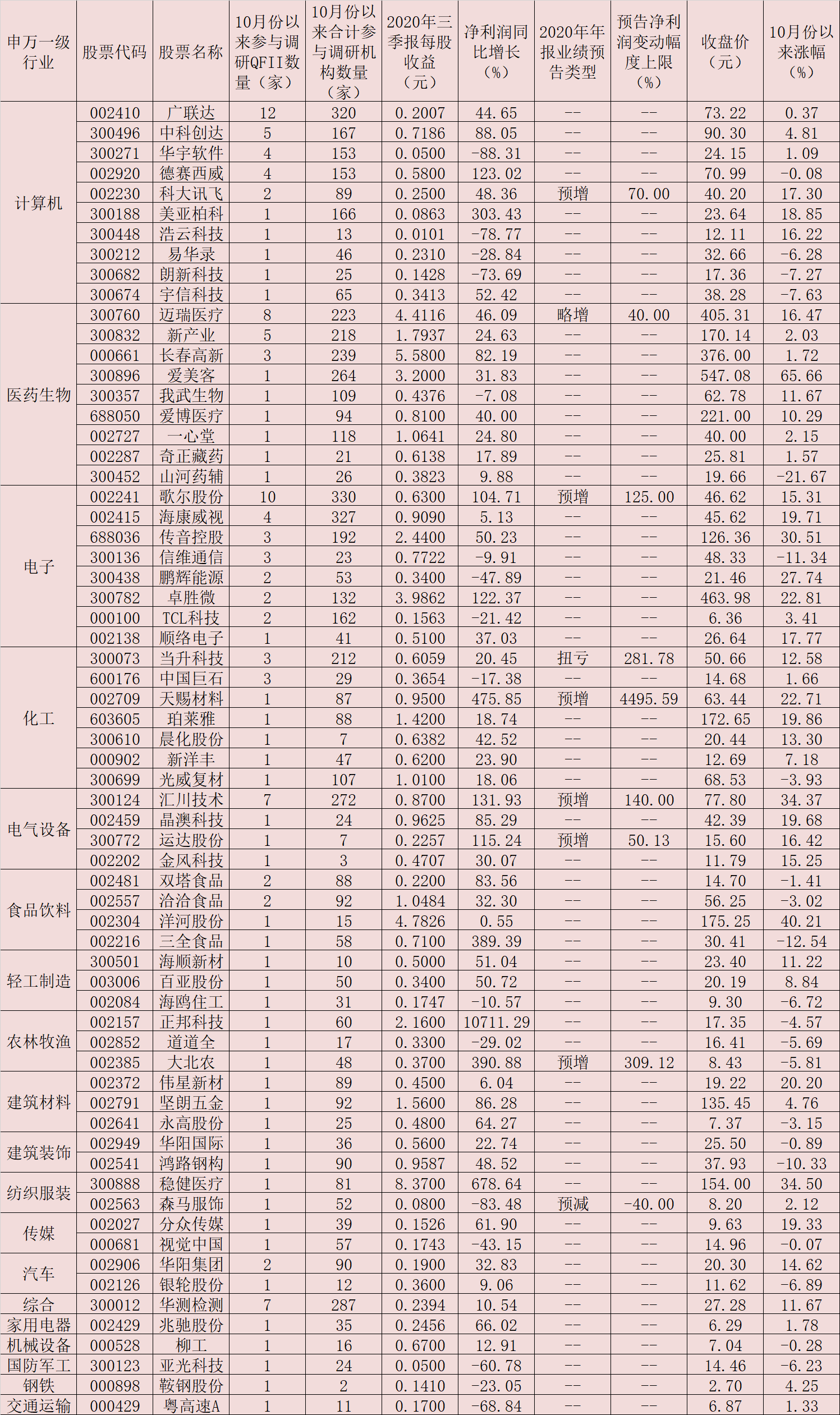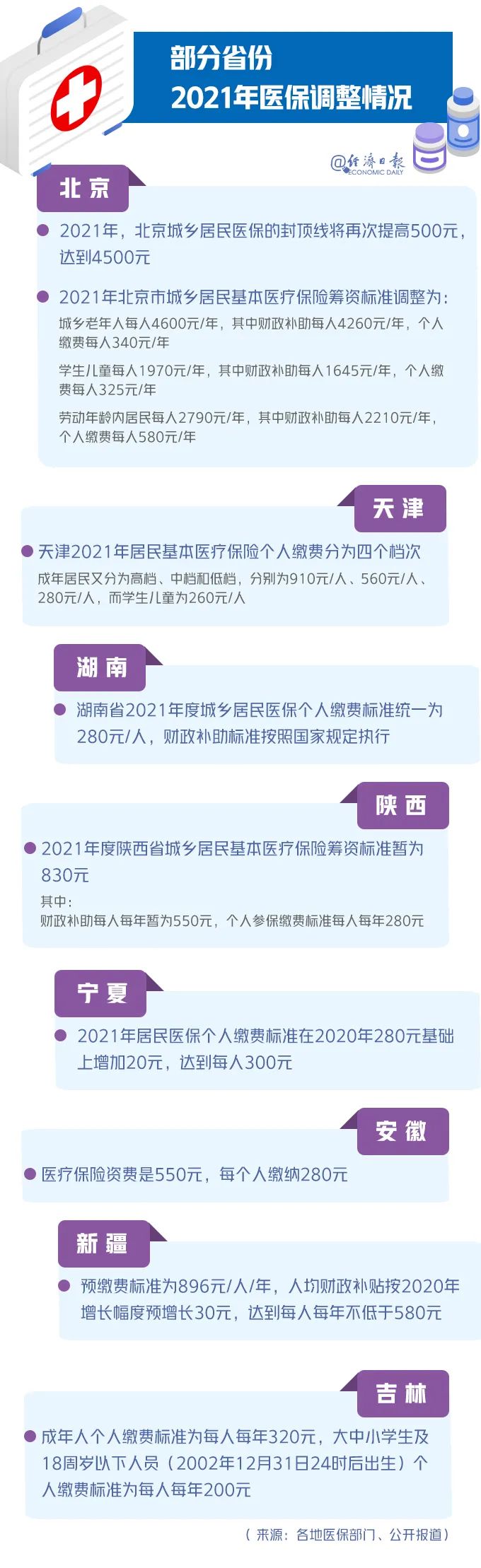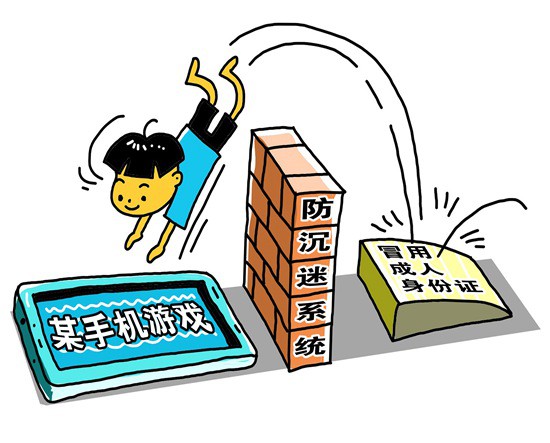原标题:风雪年关
这是我们戍守高原的别样除夕。
粘紧了门窗的帐篷,如同急促呼吸的肺,向四面鼓着、缩着,突然猛地内收,带倒了墙边的氧气罐。帐篷顶变成一张鼓皮,初是细密的沙沙声,接着无数小槌齐擂,在忽强忽弱的风嗥中,韵感渐渐凌乱。电灯在空中兀自摇曳,抖出冷寂的光,晃得整个帐篷旋转起来。丝丝寒气从不知何处的细缝微孔中针一般钻着、刀子般戳着。炉火拨得更旺,盖过电灯的白,映红了4张棱角分明的脸,几只大手围拢起火炉,进行着热能的传递。
帐篷外,海拔4500米的驻训地仿佛只有风在叫、雪在飞。
天地一片苍茫,分不清山与湖、河与路,恍若混沌之境。令人恍惚的是,落地后白得刺眼的雪,在空中却显得灰暗。风卷起雪沫漫地而行,带着吞没一切、冻结一切的决心,本就枯萎的草场被大雪压住了一切生机。
风雪突然狂骤了几分,能听见帐篷吱吱呀呀的颤抖声。几个黑点在朦胧的视野里蠕动,仿佛经过漫长的等待,黑点渐渐近了,近了。“是牦牛!”惊奇的呼喊伴着更剧烈的喘息。牦牛都低着头,用犄角犁划着风与雪织就的幕布,短而粗壮的四蹄在雪野中跋涉。它们迈着缓慢的步子,就像度着缓慢而平常的岁月。飞雪笼罩了牦牛群,大大小小的雪块凝结在角上、背上、身上、尾巴上,它们似乎忘记了饥饿,忘记了寒冷,靠毛发和皮肤抵御着亘古的酷寒。在这荒芜的高原,它们顽强地活着,存在着,顶天立地。
营地里,为帐篷加固除雪的工作已经完成,炊事帐篷传来器皿的碰撞声,风雪的管弦音合上了金属的打击声。油开始沸腾,烟气氤氲着,是馋人的肉香。高原是天然的保鲜库,营地菜窖里满满当当,整齐摆列着各类食材,这阵势预示着春节即至。一位列兵从菜窖出来,脸上白里透着红,他怀里拢着蔬菜——白萝卜、红辣椒、绿白菜——这将是他第一次在高原过年。
傍晚提早到来,上尉倚在床头,打开没有信号的手机,翻看着儿子的视频,露出了两排大白牙。小宝贝周岁生日就在正月里,买什么“迟到的礼物”送给家人,他还在举棋不定。上等兵听过《雪落下的声音》后,翻开了已卷边的高考复习资料。中士趴在行军床上给女友写信,爱情的甜蜜挂在眉梢。他床下柜子里已攒了十几封信,这些信将在休假回家时当面交给她。
不同于外面彻天彻地的白,营地中间稍大的帐篷里,却是个红色的世界:灯笼、红纸、彩灯、窗花、中国结……这是前一天外出采买的收获。小秀才正挥毫泼墨写着对联,地上已晾着几副,能看出写的是欧楷,词句间皆是豪言壮语和家国之爱。两个士兵正在排演一个相声,这将在稍后的小晚会上呈现给大家。晚会虽小,内容可绝不简单,手写的节目单上,有唱歌、舞蹈、武术表演,还有魔术、川剧变脸。一句朗诵词飞出了帐篷:祖国和人民把我们牵挂,风雪高原也有暖暖的家。
最南边的那座帐篷,门帘刺啦一声撕开,一位俊朗的士兵出来,抖动几下腰身,仔细粘好门帘,背着枪披风戴雪地向营门走去。风似要把他吹倒,能看出他在用力保持着昂首挺胸的姿态,雪地里留下一行整齐而均匀的脚印。走到营门口,郑重敬礼后,他接替上班哨兵站上了哨位。风雪更狂了,哨兵的棉帽、面罩和大衣很快覆上了白色,唯有白色睫毛下那双黑色的眼睛,依旧炯炯地睁着、亮着……(■孙利波)